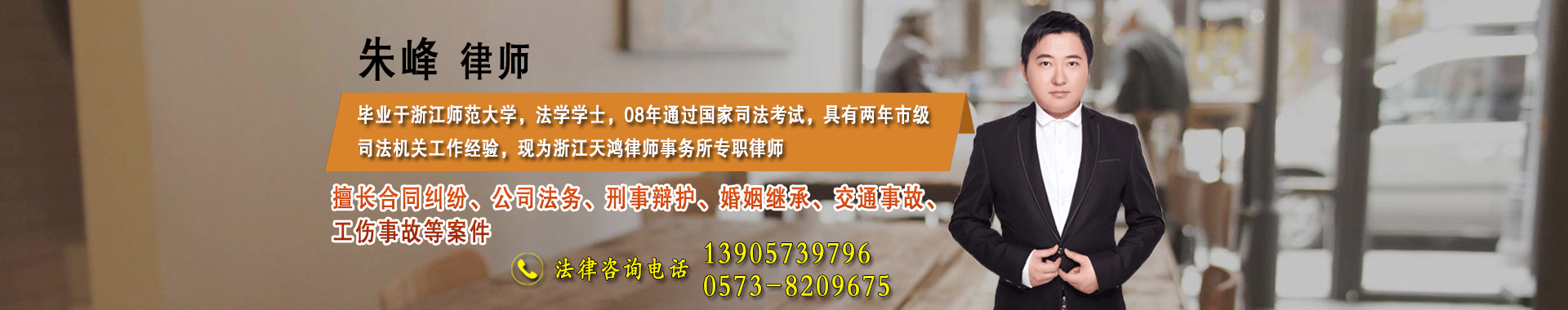【涉外合同】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来源:嘉兴专业律师 网址:http://jxls.viplaw.cn/ 时间:2015-12-15 17:12:38
【涉外合同】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对于涉外合同立法与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要想很好的解决,首先应该对它作一个深入的分析。
1.如何确定合同的成立
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的成立应适用合同缔结地法,这是古老的“场所支配行为”原则的体现。第二种观点认为,合同的成立适用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即合同准据法确定。第三种观点认为,直接适用法院地法,有的还以合同准据法为辅。
笔者认为,合同是否成立应以合同成立的准据法来确定,并且不得违反法院地的强行法律规定。这里要说明的是它并不是以统一论的观点适用一个法律体系解决合同的全部问题,因为统一论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存在许多问题,现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排斥。依分割论,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未必就是一个,当合同成立与合同准据法相同时,合同成立便适用合同准据法解决,当合同应适用的法律不止一个时,合同在不同方面就会适用不同的法律,合同成立的准据法与合同准据法就可能不一致了。笔者的上述观点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第一,如果直接适用法院地法,因合同争议可能在不同国家审判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这样就会产生不同的审判结果,不符合审判一致性的原则。人们所担心的问题是,合同成立适用合同成立的准据法可能不符合法院地国家的强行法律规定。对于这个问题,因为各国法律都规定本国强制性法律和公共秩序不得违反,其违反不具有法律意义,这样即使法院依据合同成立的准据法确认合同是成立的,法院仍然可以其违反了法院地国家的强行规定而确认合同无效,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
这次《合同法》本身就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了划分,成立的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是不生效的,因此,法院地的强行法律规定是不能违反的,但它并不限制合同成立所适用的法律,而是违反法院地法时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效。
第二,依照《合同法》规定,涉外合同的争议应适用涉外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解决,涉外合同成立也可能发生争议,应以合同成立的准据法解决该争议。这样既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前面有分析),也避免了《解答》对“合同争议”的广义理解与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4条“订立合同,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间的矛盾。法院强行法律规定不容违反,这一点无需再强调,符合中国法律也是指强行法律规定,而非任意性规范。
第三,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由假使合同已经成立,以此确定合同的准据法来解决。这种观点创立于国外,但已被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这与国际上1980年罗马公约和1985年海牙公约规定中关于当事人选择条款的有效性应以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确定具有相同的意义。确定合同的成立依据是合同成立的准据法,不能将一个涉外合同首先看作一个国内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那样就忽视了涉外合同的特殊性。
第四,如果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那么合同成立本来就应该满足合同准据法的要件。虽然当事人选择法律是狭义上的合同法律适用,仅限于确定合同准据法,即确定合同效力的法律适用,但是,当事人在选择法律时,自然也应该考虑到自己签订的合同符合所选择的法律的规定,否则当事人对选择的法律就太不了解了。
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的适用法律,对于仅因合同成立发生的争议,应该依据冲突规范确定合同成立的准据法,对于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依据分割理论确定合同成立的法律,因为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本身就确认了合同的成立,只不过当事人并不是依据与合同履行适用相同的法律认定的。
第五,合同法律适用缔结地法的观点优点在于缔结地法为当事人所熟悉,而且缔结地法这一客观标志容易确定。但是,适用它有一些弊端,合同的缔结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且当事人可以任意选择,尤其对于隔地合同,其缔结地难于确定,使合同的法律适用不具有确定性。
2.是否承认默示的法律选择
默示的法律选择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明文约定他们之间的合同适用哪国的法律,由法官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和案件事实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向。毫无疑问,明示的法律选择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总是得到肯定的,问题在于:默示的法律选择在本质上是否确实是合同当事人法律选择的合意?
有人认为,默示法律选择并不由当事人作出,而是由受理案件的法官代替当事人作出。如果法官简单、武断,将会把缺乏根据,主要是他自己的主观推断强加给合同当事人;换句话说,即法官把他自己所作的“法律选择”,硬说成是合同当事人的“默示的法律选择”。
我国学者明确反对默示法律选择的理由主要在于,外国法院为了竟相适用本国法律,会过分利用其自由裁量权,来达到适用法院地法的事实。为此,我国在《解答》中将当事人的法律选择限定为“必须是明示的”。
其实,是否应承认默示的法律选择,关键在于法官的推定是否有充分而客观的根据,能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在合同中明白订立适用的法律是不很常见的,甚至象保险公司、主权国家所订立的国际借款契约中,也常常没有指明适用于交易的法律。这时,从契约文本中推断当事人之间关于准据法的默示约定,有时是可能的。就是说,虽然当事人未能就法律选择作出明确的表述,但是,作为合同当事人,一般他们都是商人,并非法律专家,其表达未必能非常准确;或者说,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确指在发生争议后,能适用某一国法律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但如果在发生争议后,让当事人去解释他们是否能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选择时,因这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双方利益有明显的不一致,作出的解释往往是大相竟异的。
从历史上看,杜摩兰在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时,就有当事人未直接表明适用何种习惯法时,法院也应推定其默示的意向。从国外的情况看,同意默示的法律选择仍然是一种主流。1980罗马公约在第3条第1款规定:“法律选择必须通过合同条款或具体情况相当明确地加以表示或表明”。1985年海牙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的选择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者从合同的规定和当事人的行为整体来看可以明显的推断出来”。
从理论上来说,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实质,并非不认同默示选择;批评意见也指出,之所以不承认默示选择在于它给予了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会不利于公平确定合同的准据法;但是,如果就这样否定了默示的法律选择,是否考虑到这也可能损害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呢?
因此,如果能确定默示的法律选择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应当得到法官的认同;不能因为法官可能有偏见而否定当事人的法律选择,而应该通过对它作出限制性规定,进而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其推定不能只以某个合同条款或某个案件事实为根据,必须以对所有条款和案件事实的综合考察为根据,并且此种推定必须是明显而合理的。
更深层意义上,两个公约对默示法律选择的承认,也显示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我们不应将对某些国家在实际审判中的霸权行为的批驳,写入我国的法律,从而否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这样也不能限制外国法院如此作出判决。
在实务操作中,如果我们能承认默示的法律选择,也会从根本上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至于默示的法律选择很大程度上导致法院地法的适用,即使我国法律不承认默示的法律选择,也不能阻止外国法官这种作法;如果我国法律承认了默示的法律选择,我国法院也可以因此确立本国法律的准据法地位。毕竟,我国当事人在参与涉外合同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因合同在我国境内签订并执行时,与外国当事人默示选择中国法律,而因种种原因,未能将其选择明示化。至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确保法官不会滥用当事人对默示选择的推定,可以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规定,要求确定默示的法律选择必须综合合同条款并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能够合理确定地表明,从而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